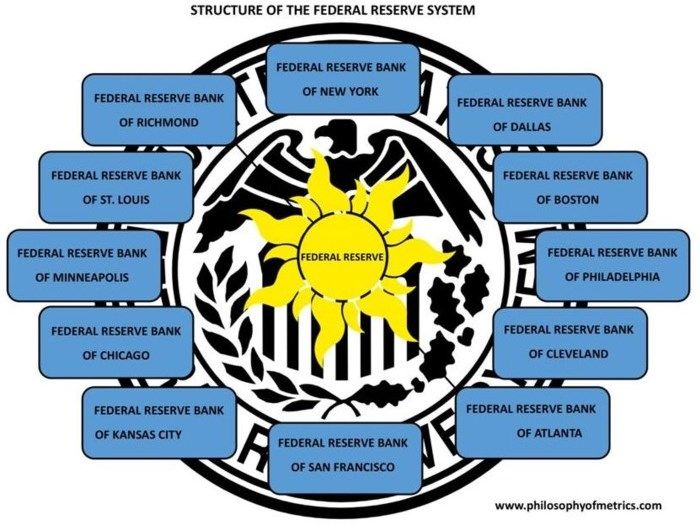
|
| 美國從小布什總統任內,國家債務便年年快速上升。 |
中評社╱題:余英時的“幫派”與“典範” 作者:黃光國(台灣),台灣大學榮譽教授
【摘要】在當時的美國,“哈佛幫”的理論是代表主流價值的“常態科學”,反戰學生的觀點,則是必須被設法“擺平”的“異例”。更清楚地說,由於常態科學是由某種典範所宰制,典範總是受到絕對的信賴。但它與實踐結果之間,總是存在著明顯的差異或“異例”。“常態科學”的主要工作,便是經過恰當的調整,來解決這些反常的異例,以使典範不受損害。
一、紅學研究的“典範”
龔忠武在〈辛丑元年祭〉的長文中,敘說他跟余英時之間“亦師亦友”的關係:1966年,他從台大到哈佛,成為費正清門下的一名研究生,余英時正好從密西根大學轉聘到哈佛,為罹患嚴重精神病的楊聯陞代課。兩人除了師生關係之外,周末還經常到他家打牙祭,並參加圍棋俱樂部的棋會。在1968年-1969年,余氏祇是個在哈佛代課的助理教授,在哈佛的去留問題,成為他最大的心理壓力,一度情緒十分消沉,香烟不離手,藉烟消愁,並且不諱言,可能回到香港教書。
1969-1970年之交,海外留學生爆發了保釣運動,龔忠武發現:余氏在校園裡老跟在費正清後面,做說服反戰學生的工作。余氏是圍棋高手,兩人閒聊時曾對龔忠武說:棋如人生。他現在正為他今後的學術生涯,下一盤大棋。
從1970年起,正值中壯年的余氏,為了打入美國學術界主流而拚命著書立說,企求揚名立萬。在這段期間,余英時完成了有關《紅樓夢》研究的三篇文章,一起收錄在《歷史與思想》一書中。其中最重要的一篇〈近代紅學的研究與紅學革命〉(1974),余氏引用孔恩(Thomas Kuhn, 1922-1996)在其名著《科學革命的結構》中所提出的“典範”之說:
“典範”可以有廣狹二義:廣義的“典範”指一門科學研究中的全套信仰、價值、和技術(entire constellation of beliefs, value, and techniques),因此又可稱為“學科的型範”(disciplinary matrix)。狹義的“典範”則指一門科學在常態情形下所共同遵奉的楷模(examplars or shared examples)。這個狹義的“典範”也是“學科的型範”中的一個組成部分,但卻是最重要、最中心的部分。
在這篇文章中,余英時認為:紅學研究史上出現過兩個占主導地位而又互相競爭的“典範”,第一個“典範”可以蔡元培的〈石頭記索隱〉為代表,其中心理論是以《紅樓夢》為清初政治小說,旨在宣揚民族主義,弔明之亡,揭清之失。第二個“典範”認為:《紅樓夢》是曹雪芹的自敘傳,此說起源甚早,直到胡適的《紅樓夢考證》問世,才成為一種新的“典範”。
對於科學哲學稍有瞭解的人都知道:孔恩所說的“科學革命”是指“自然科學的革命”,他並未提到“人文學”是否適用此一概念。“紅學研究”中,不管是“索隱派”也好,或是“考證派”也罷,其實都是中國傳統考據學的餘緒,跟孔恩所說的“科學革命”並不相干。
余英時在提出他的“紅學革命”說時,不用他最崇拜的柯靈烏歷史哲學,反而非常勉強地採用孔恩的“科學革命論”,很可能是因為他注意到孔恩有關“常態科學”的主張:
孔恩的研究充分顯示一切“常態科學”(normal science)都是在一定的“典範”指引之下發展的。科學家學習他的本門學科的過程,通常並不是從研究抽象的理論和規則入手。相反地,他總是以當時最高的具體科學成就為楷模而逐漸學習得來的。這種具體的科學成就在今天是以教科書的方式出現的:在以往則見之於科學史上所謂經典的作品,如亞里斯多德的物理學(Aristotle′s Physica)、牛頓的原理(Newton′s Principia)等等。
科學史上樹立的“典範”的巨人一般地說必須具備兩種特徵:第一、他不但在具體研究方面具有空前的成就,並且在這種成就還起著示範的作用,使同行的人都得踏著他的足跡前進。第二、他在本門學術中的成就雖大,但並沒有解決其中的一切問題。恰恰相反,他一方面開啟了無窮的法門;而另一方面又留下了無數的新問題,讓後來的人可以繼續研究下去(即所謂“掃蕩工作”mop-up work),因而形成一個新的科學研究的傳統。
在《歷史與思想》一書的“自序”中,余英時很清楚地表明,他最大的心願是“明天人之際,道古今之變,成一家之言”,成為科學史上樹立“典範”的巨人。他十分明瞭:不管“紅學革命”在學術上有多重要,他再努力搞“紅學研究”,都不可能成為樹立“典範”的巨人,他必須另闢蹊徑。在他所處的那個時代,他要如何找出自己的“道”?
二、“現代化理論”的典範
依照孔恩的理論,科學社群(scientific community)是指在某一科學研究的領域內,探索目標大致相同的科學工作者。在常態科學階段,科學社群通常會信仰同一個典範,接受同樣的教育,擁有共同的語言,運用同樣的方法,探索共同的目標。科學社群是連接個別科學家與整個社會結構的橋樑。科學家個別的發現,必須經過科學社群才能與其他社會團體產生互動。這也是常態科學時期科學得以迅速發展的重要因素。
學者要加入某一科學社群,從事研究,必須從研究其典範入手。他們在進行研究的時候,可以這套共有的典範為基礎,信守同樣的研究規則及標準程序。這種信守的態度以及因而產生的共識,是常態科學發生與延續的先決條件。任何科學研究的領域,都必須產生研究典範,才能從事進一步的研究,這個研究領域才有可能趨於成熟。
在哈佛思索他個人去留問題的時候,余英時必然已經注意到:哈佛大學的科學社群正在努力建構“現代化理論”(modernization theory)的研究典範。他們用二分法,把全世界的文化分為“傳統”和“現代”兩大類,美國是全世界“現代化”的領頭羊,全世界文化變遷的大方向就是“現代化”,由他們的文化傳統,朝美國的方向轉變。
當時哈佛大學社會學系的教授英克勒斯(Alex Inkeles,1920-2012)可以說是為“現代化理論”樹立“典範”的巨人。他還設計出一種“個人現代性量表”(individual modernity scale),廣為非西方國家所採用,我在台灣大學心理學研究所念書時,在楊國樞教授指導下所完成的碩士論文〈個人現代性程度與社會取向強弱〉,都採用了他所創立的研究“典範”。
英克勒斯精通俄文,二次大戰期間,他曾經為美國情報單位工作,任務就是解讀蘇聯出版品及廣播中的重要訊息。在冷戰時期,英克勒斯本人的研究主題卻是蘇聯的社會變遷。他本人的著作也大多與此有關。建構“現代化理論”,並不完全是出自學術目的,更重要的是要配合冷戰時期美國政府的政策。
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費正清(John. K. Fairbank, 1907-1991)的背景也類似於此。費正清是美國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。1941年,他被美國情報協調局徵召,擔任情報研究及分析工作;1942至1943年間,他以戰略情報局官員的身分,兼任美國駐華大使特別助理。1946年返回哈佛大學任教,並於1955年成立主持“東亞問題研究中心”。
依照孔恩的理論,常態科學時期,科學家的主要活動是在一套固定的科學標準下,將心力集中在特定的範圍,精鍊典範,加速科學的進步。科學研究中的解謎活動,其答案經常是在預期之中的;解答常態問題,通常祇是用一種新的方法達到預期的目標。這樣的工作必須超越各種觀念上的、研究方法上的或研究工具上的障礙。在內容上和在時間上,常態科學都佔據了科學活動很大的部分。這時候,科學家的主要研究動機在於他相信:祇要我夠高明,就必定有解答。
在1970年代,余英時既然已經下定決心,要留在哈佛並“打入美國學術界主流”,於是回到柯靈烏的歷史哲學,集中全力,用他“先驗的想像”,建構出他的核心理論“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”。這時候,有沒有人覺察到他這種“歷史的建構”方式有問題呢?有的。這個人就是和他有“亦師亦友”關係的龔忠武。
三、“哈佛幫”的危機與中國學
龔忠武《在哈佛的激情歲月》一文指出:
1968年接連不斷的越戰災難使許多美國大學生深深感到,整個天都要塌下來了:過去他們深信不疑的美國基本價值、教育體制和運作機制、政學關係、建立在言論自由價值上的大眾傳媒,現在都面臨信任危機,都需要徹底從新審視。一時之間,美國人引以為傲的文化突然變得一無是處,都出了問題!
他們的基本理念是美國介入越南的戰爭,是一場違反正義的侵略戰爭,根本不值得美國人民支持,不值得美國人花錢,讓美國青年去送命!他們基於學者的良心,一定要堅決反戰。他們從理論上分析:導致美國陷入越戰泥沼的原因,是美國狹隘的國家利益,是美蘇兩極僵硬的反共反華冷戰思維,是敵視共產中國和在東南亞圍堵中國共產主義的多米諾骨牌理論。費正清一手建立的中國學,就是圍堵中國理論的主要構成部分!
從孔恩的理論來看,這時候“哈佛幫”建立的理論已經面臨了“危機”。然而,在當時的美國,“哈佛幫”的理論是代表主流價值的“常態科學”,反戰學生的觀點,則是必須被設法“擺平”的“異例”。更清楚地說,由於常態科學是由某種典範所宰制,典範總是受到絕對的信賴。但它與實踐結果之間,總是存在著明顯的差異或“異例”。“常態科學”的主要工作,便是經過恰當的調整,來解決這些反常的異例,以使典範不受損害。
當時龔忠武的反戰同學在關心亞洲問題學者委員會學報(the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)和“哈佛校報”(the Harvard Crimson)上,和費正清及他的助手沃格爾(Ezra F. Vogel)進行了針鋒相對的論戰。
1968年10月間,辯論的焦點,是質問費正清所主持的東亞研究中心,為什麼要培訓在當時反戰學生深惡痛絕的中央情報局人員?他們認為,這根本違反了學術的自由和獨立性,是可忍,孰不可忍?費正清被迫回應說,雙方的合作是互利的,中心可以從國防部得到經費支持,並且可以從中央情報局獲得機密資料!費的回答徹底暴露了美國“中國學”的真實面貌!原來所謂客觀獨立的學術研究祇是幌子,“中國學”骨子裡祇不過是美國外交政策的一個工具,是為美國的亞洲政策提供理論依據,如此而已!
龔忠武說,當他知道這些事實,他的思想陷入了嚴重的混亂狀態;嚴重到失掉了論文的立場、大方向和前景,不知道應該朝什麼方向來引導論文的論證。“這時我感到的是迷惘、失落、焦慮,陷於嚴重的思想和心理危機,同我初到哈佛時的那種意氣風發和樂觀自信,適成鮮明的對比。我的哈佛之夢,開始幻滅了!”
|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