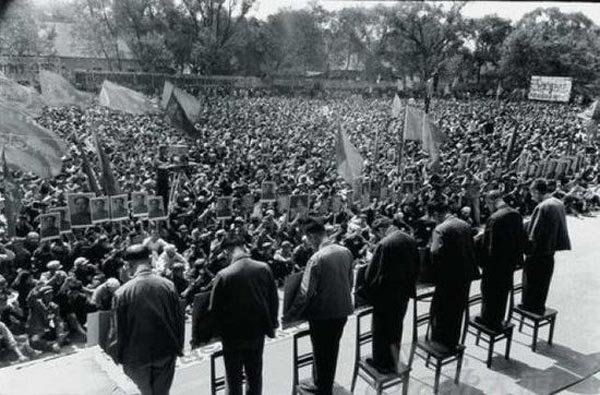| 【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第5頁 第6頁 第7頁 第8頁 】 | |
| 歷史反思:大多數紅衛兵為何不道歉 | |
http://www.CRNTT.com 2013-06-22 10:42:11 |
不可否認,王祖鍔當年對不平等的感受是真切的。但這種不平等,並非自“血統論”大旗出現後才有,而是歷次階級鬥爭日積月累的結果,“血統論”不過是將其推向了高潮而已——1967年元旦,北京“老紅衛兵”曾以“革幹子弟聯合行動委員會”名義發表全國通告,將他們的組織路線規定為:“(1)第一階段由中共中央、國務院、解放軍、省市委幹部子弟組成;(2)第二階段由基層組織(地委專署與公社)幹部子弟組成;(3)第三階段吸收全國工農兵和出身他種家庭而政治表現好的”,等級之森嚴躍然紙上。這種等級刺激,最終使許多寒門子弟出身的造反派紅衛兵,多年來一直堅持相信:自己當年的所作所為是“為社會公正和人與人的平等而鬥爭,這是值得驕傲的”。(此外,對造反派紅衛兵而言,因文革後清查“三種人”等政策,披露自己的身份還存在給自己的生活招來麻煩的可能,這也是一些造反派紅衛兵不願意出來道歉的原因。) 02 只有廓清歷史真相,才能促成紅衛兵的集體反思 前述保守派和造反派的自我辯護有沒有道理?有一定的道理。但這種辯護遮蔽不了最要害的問題:無論是保守派,還是造反派,在文革期間都曾對社會有過巨大的破壞作用,盲目“破四舊”對文化的摧毀不可估量,隨意打人、遍地武鬥死傷者不計其數……這些惡果,不光造反派有責,保守派也有份。要促成紅衛兵的集體反思,關鍵在於廓清歷史真相,將歷史責任具體化。 要明確具體是誰的責任,就不能含糊其詞甚至張冠李戴移花接木到1967年上半年,因為得不到中央文革的支持,“保守派”紅衛兵基本上已經退出了文革舞台。此後,造反派內部又分化出溫和造反派和激進造反派,大量慘烈的武鬥,即發生在這些溫和派與激進派之間。如重慶市的大規模武鬥,就大部分發生在原造反派“八一五戰鬥團”分裂為“八一五派”和“反到底派”之後,個中原因,造反派領袖之一的周家瑜的解釋是:“在衝擊政府機關奪權後,因為內部權力分配出現分歧”。此時,造反派們用來為自己辯護的“為爭取平等而鬥爭”,早已不複存在。也就是說,必須對造反派們當年的具體行為,做具體的分析,如此,即不難看出“為爭取平等而鬥爭”這樣的辯護詞,在造反派發起的每場具體武鬥中是否契合。這種具體分析,對保守派紅衛兵也同樣適用。 另外,還應注意:造反派做的就是造反派做的,保守派幹的就是保守派幹的,不能含混其詞,更不能張冠李戴移花接木。但因為某些歷史原因,此類含混其詞的問題很常見。譬如老舍之死,就很有必要搞清楚。老舍自殺前,曾遭到紅衛兵猛烈的批鬥毆打,一些相關的回憶文章,大都將這些紅衛兵稱作“造反派”,如老作家浩然說:“老舍就站在人群中,造反派點名往外揪人”。但根據一位當日參與批鬥老舍的女紅衛兵的回憶,這些紅衛兵未必是造反派,更有可能是保守派。這位女紅衛兵在接受《太平湖的記憶:老舍之死》一書作者傅光明的採訪時,沒有透露自己的姓名,而僅以“她”指代。據“她”回憶: “1966年我在女八中是老高二,是學校文革領導小組九個成員之一。我在文革前是學生會體育部長,所以文革一開始就被選進領導小組,當時出頭露面多一點。但最主要的領導是白乃英,我一般只管管組織站隊,喊喊口號什麼的。……(女八中)在石駙馬大街,民族宮那邊,後來叫158中,現在好像叫魯迅中學。當時是女中。我記得那年8月21、22號,天氣特別熱。白乃英說市文聯有人打電話來,讓我們去造反。她叫我帶著人過去、從文聯來了兩輛大卡車把我們接去的,大約有150人。……我覺得當時的人有理想,不像現在的人這麼忙忙碌碌;當時我們的感覺就是自己將來是社會的支柱;我們出身好,什麼事都衝在前面。本來我可以不插隊,但堅決要求插隊。肯吃苦。可到了社會上完全不是那麼回事。當時認為黑幫就是敵人。太年輕了。我是有代表性的。比我小兩三歲的人就更幼稚了。串聯回來,對有些事自己有看法了。1966年8月16日,毛主席接見紅衛兵,我們還是糾察隊(筆者注:“她”的時間記憶有誤,毛澤東首次接見紅衛兵,是在8月18日,第二次是8月31日,女八中所在的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西城分隊,也就是“西糾”,成立於8月25日),站在隊里特自豪。”(鄭實、傅光明編著,《太平湖的記憶:老舍之死》) |
|
|
相關新聞:
- 文革紅衛兵為當年惡行登廣告道歉 (2013-06-20 12:15:27)
- 陳白塵“文革”日記:個中況味天人共知 (2013-05-26 09:47:48)
- 文革記憶:清華批鬥王光美始末 (2013-05-25 10:30:04)
- 鄢烈山:我記憶中的文化大革命 (2013-05-19 09:15:07)
- 江青“禦用攝影師”悲歡史 (2013-05-13 15:08:23)
- 親歷者講述:為“文革”宣傳畫寫前言 (2013-05-02 13:53:37)
- 傅高義對談秦輝:還原歷史的真實圖景 (2013-05-02 11:24:33)
- 傅靖生:文革中 我鬥了我爸 (2013-03-29 12:29:11)